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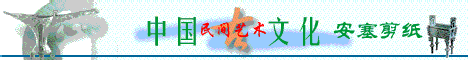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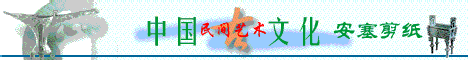

|
陕北行,八十年代西行漫记 三暮 |
||||
|
六、七十年代我在延安生活了多年,因邻居老高盛情之邀,也想看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北的变化,还听说他的女儿不幸得了骨癌,我在北京王府井药店给他买了专治骨癌的特效药“顺伯”,便匆匆上路了。 |
||||
|
|
 |
 |
|
|
|
1985年4月29日从西安走的那天早上,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第六感官显灵。车开到高陵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一只鸽子冲向高速驶来的汽车,把大轿车前挡风玻璃撞碎,可见这股冲击力有多大。司机只觉得一团“黑旋风”向自己扑来,下意识低头,眼睛上角被玻璃划破,鲜血模糊了双眼,险些酿成车祸。当时我正低头整理东西,那死鸽子夹杂着碎玻璃像炮弹一样从我头顶呼啸而过,不然我也可能满脸血肉模糊,幸好只有碎玻璃碴把我的鞋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可坐在我身后三排远的一位老农却倒了八辈子血霉,碎玻璃碴糊了他一脸,划伤鼻子,血流如注,死鸽子拽在他的前胸,人血、鸽子血染红了衣衫,那个狼狈相就别提了,还好,其他乘客无大碍。事后副司机替换开车。这“炮弹”要是在低一厘米,把司机眼睛扎瞎,车撞在树上或翻车……,乘客们都在纷纷议论着假设的后果。我坐在前排,事后细思恐极,倒吸一口凉气,多亏了司机盲眼忍痛急踩刹车,保护了全车乘客的安全。 此时,透过空荡的前车窗,可以看见洛川附近已种上的油菜开黄花了,但这里的油菜比汉中长的要低矮的多了。原先陕北吃油,只有小麻与黄盖。油渣舍不得喂牲口,做了“麻汤饭”。麻汤饭虽香,入口回味无穷,可那是一种舌尖上的“诱惑”,吃完了就不是你自己了,“尿憋咧”能把人急死,转着圈跺脚,干着急,死活撒不出尿。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我再也不敢吃麻汤饭了。 三个多小时后,长途汽车抵达洛川停车吃饭、上厕所。这时,一群卖煮鸡蛋、吹饼的婆姨、女子们蜂拥而上,争相叫卖。“我的鸡蛋早上刚出锅的,新鲜,叔叔、大哥、大爷买我家的吧!”卖炊饼的婆姨也不甘落后,“哎,刚出炉的烧饼外脆里香,过这村就没这店,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从这些状况可以看出陕北经济两点信息:⑴政策放活,农副产品增多。⑵由于是山区,工业不发达,购买力低下,国家收购也有限,出现卖不出去或不好卖的现象,仅当时在安塞一元钱能买十五个左右鸡蛋,而且还要操心打问买家。 在车上颠簸了多半天,下午终于到“家”了。啊!革命圣地延安,插队一别十二载,我又回来了。经过各个历史时代,你依然雄姿屹立,你检阅着延安儿女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延安市容大变,让我这当年的“老”延安都不认得你了。从“土气”的窑洞群中拔地而起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延安大桥也不只宝塔山前这一座,延河畔上相继建出三座桥;挨着宝塔山东南角下又开辟出一片新市区,原来那里是一片野草丛生。夕阳西下站在延安大桥旁,那山环水,水映山,青峰倒影,傍依河边围栏,波光粼粼的延河水,泛出高原泥土特有的芳香,第二故乡的情怀油然而生。 七律•怀念延安 黄土高坡坡顶天,崖前窑洞洞相连。 黎明日眺西坡处,旁晚夕阳东照岩。 曲径羊肠通故里,隔山相望守心田。 鸡鸣犬吠闻相久,呐喊隔山见面难。 乡村插队闯三关,见雨经风战鼓酣。 书记谆谆循善诱,村农处处授千千。 初来乍到生奇异,点籽耕犁握主鞭。 走过中年方已醒,三十弹指一挥间。 宝塔山东北角的清凉山原是新华社的所在地,这里有万佛洞,现正在修葺,文革后期一直没有公开开放。范仲淹曾在这石壁上题词、作诗。他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曾向仁宗赵祯上条陈十事,要求改革当时弊政。他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其《岳阳楼记》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所传诵。他的词,有的写边塞生活,有的写羁旅情怀,或苍凉悲壮,或缠绵深婉。 |
||||
 |
 |
 |
 |
 |
|
延安除了好的一面也有阴暗面,市容太差,侏儒和乞丐死缠着你不放,不讨要出个毛八分的誓不罢休。还有惊现光天化日之下,灰汉圪蹴在繁华市中心延河大桥上拉屎,难道他就是那个“享誉”安塞县城里“精股子王成”吗?灰王成十冬腊月都不穿衣服。可怜人必有可怜处,人们见了他都会给他要饭的钵子里放些吃的。你还别说,多年不见灰王成,时不时的挺念记他,也不知他尔格过得还好吗?当然,这只是几十年前的轶事,全当茶余饭后的笑料。如今的延安城已经和现代化大都市没什么两样。 回到蔡阳坪村里俯视全庄,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那时哪有公路啊,人们看见汽车就跟看见什么稀罕物似的,追在后面满世际跑,那时看见汽车都属于“天方夜谭”。现在一辆班车正巧从村前公路经过都让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世道变了。瞧,公路上边十来米高的脑畔上那一排石窑,就是当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彭德怀、朱德的指挥部,延安保育院也在这村里安营扎寨。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村里拍了好几天戏,乡亲们都奔走相告“李德胜(毛泽东)又回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也回村里来寻根,看看马背小学和保育院的窑洞尔格还在不在。 |
||||
 |
 |
 |
 |
|
|
村对面“大平川”的坡畔上,苹果树是我们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时只是长到腰眼的小树苗,如今已结出苹果了。承包前,偷毁的不成样子,承包给个人六年来一共才交给队里200多元钱,主要是果树的品种不符合人们的口味儿,再加上树苗被羊啃的都长不成果林了。近处那沟里正开花的是梨树,树的主人拓普安全家都搬到县城里居住,农村人口城镇化在延安八十年代初已经悄悄地开始发展起来。 真没想到,我们村沉睡千年的大地,地下会有那么多的石油?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油老板都云集到陕北来发财。路边的磕头机昼夜不停地运转,滚滚的石油输进储油罐,石油工业的发展给陕北带来了生机,就像美国西部的淘金热,陕北的土地只要有立锥之地都竖起了油井架。在陕北,黄土面比沙金都值钱,谁占有了黄土地谁就占有了财富。站在黄土高坡极目远望像树林般的一片片井架,全县已建成油井1376口,巍巍壮观。石油工业的发展使脆弱的生态平衡开始遭到破坏,废油废水流入延河,这难道是中国工业应该走的道路吗? 因为石油,人们开始富足,吃糠咽菜的日子是老奶奶给孙儿们讲故事的佐料,杀鸡、宰羊、吃白面,几年前想都不敢想,来了客人不准备这些都觉得脸上无光。可是就在几年前,村里的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当年,我和村里的人们一块照相,就这照片,现在让我看了都泪流满面。穿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个个破衣拉褂,比济公穿的还寒掺。野菜糠窝窝吃了上顿没下顿,顿顿尽灌个水饱。什么?你说我尽吹牛,特惨的照片吓得我都没敢往上摆,喝口烧酒斗胆只能偷偷在没有人的地方拿出来看看。村里生活最苦的就属南金山家,全家九口人,没吃、没喝、没穿的。寒冬腊月,在窑里,碎脑、猴娃们个个都“赤膊咧”“精股子”,依偎在有点火星的暖灶台旁;全部家当,炕上只有一张破席子,两条脏被子,九口人,一套像样的衣服,谁外出谁才能穿。那时,政府也没少救济他们,新席子让老南一点点掰开,当火柴棍点旱烟抽了,买不起火柴呀;救济的小米,有了吃干饭,没了灌水饱。乡亲们都说老南家不会计划过日子,可您想想,饿久了的人谁见了小米不想吃顿饱饭呀。终因生活穷困潦倒,老南已经没有信心再活下去,喝了农药悄悄躲到山里死了。他家的贫困生活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激励我不能忘掉过去。 |
||||
 |
 |
 |
 |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政策放活,群众解决了温饱。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单干,积极性提高了,产的粮食增多,国家甚至都不收购了。粮价下降,小米单价0.18-0.20元,黄米、软糜子单价0.25-0.28元,玉米单价0.09-0.12元。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业,远离城镇,钱不好挣,农民就靠用鸡蛋换点零花钱。鸡蛋国家也不收购了,一元钱十四个。单干有单干的好处,也有缺陷,贫富差距拉大,但是贫,并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人们将将迈入温饱。单干后缺少劳动力的家庭种地困难,所以发展人口是当务之急。主要是发展男劳动力,生不出男孩誓不罢休,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有的家庭甚至躲到深山老林中当黑户。多子女家庭主要是多女孩家庭重新沦落为贫困户。在这种背景下,陕北还保持着几千年生活习俗,那就是崇拜生殖,在陕北民间文化艺术作品中,安塞农民画、民间剪纸里都有所反映,包括石刻和土刻。照片里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上面两幅照片是老高家庭十年间的对比。他一个得骨癌的女儿虽然用了“顺伯”,但终究耽搁太久了,没能挽救过来,临死前,疼得她紧紧攥住娘的手,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娘,我疼,救救我吧!”母亲无助地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女儿正值芳华妙龄,死时只有21岁。 农村、农业、农民,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朝代更替所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没离开三农问题,变革的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生产力关系的调整,从革命初期的单干,到夺取政权后实行集体化,再到单干,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陕北农村自从单干后,农田基本建设困难重重,即使想在自己的土地内搞农田基本建设,因为涉及到别人的土地,如水渠、梯田等也就作罢了。现在,农民在以前搞下的农田基建的基础上种田劳作,不考虑长远规划,干一天是一天,协作仅限在家族之内。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当然在陕北眼下还高不到哪去),这种单干的形式是否还适合呢?即使在一家一户的范围内,有限的资金也买不了多少肥料、农具、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因为这里钱的来源受到限制。农村工业几乎是零,就业难,卖家多,卖粮难,卖农副产品更难,供大于销。总之,一没销路,二没资金,从农业银行借出的贷款,有的人干脆都用来赌博。 随全国工业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现代文明的标志“电”,就像长满触角的巨大怪物,伸展到四面八方。高压输电线已经到了离我居住的村子仅五里远的肖官驿村,听说明年就能到本村蔡阳坪。在过去我们都不曾想过的事,且不说点上灯泡后窑洞更加明亮,而且给以后的现代化生活提供了动力和能源。当年,在无电的社会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被压抑到了极限。鸡叫三遍天将蒙蒙亮,生产队长从后庄一直吼到前庄,“哦——杂务哩!”睡眼惺忪的人们机械地爬起炕,披上衣服,踉踉跄跄推开窑门,扛上镢头直奔山里。早饭、午饭都在山里吃,直干到太阳落山,天擦黑,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回家,还得打起精神做晚饭,饭后早早地钻进被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做着太阳的奴隶,地还是那些地,粮还是那些粮。那时,我最忌讳的就是夏天,昼太长,劳作整天困的睁不开眼,当然最喜欢的还是那秋冬季。 陕北是唯一还保持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地区,最根本的方面自然首推黄土地传统文化积淀的雄厚渊深。具有悠久历史的陕北地区,夏、商、周三代时,就有人逐水草而牧游。秦始皇高筑长城之后就有人定居,发展种植业。这里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这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仰韶、龙山文化和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遗迹遗物,商代以来的文物十分丰富。在艰苦的外部自然环境中,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与命运抗争搏斗,取得了生存与发展的胜利,同时,地域的特殊性使得陕北文化积淀中还有另一个鲜明的特色——历史上长时期多回合的诸多民族交叉融合,使这一地域的文化既有汉民族文化特点,又有北漠草原的文化特色。在封建社会后期明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形成历史上的交通封闭和文化封闭,使其其它地域早已失传的古老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在这里民间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在陕北农村大部分家庭里很少有像样家具,常见的窑掌里有几个木箱,上面放些被褥,几口大缸里面淹些酸菜,至多有些小炕桌、衣柜。炕是家庭生活的源泉和中心,在炕上吃饭、睡觉、炕干潮湿的粮食、老母鸡抱窝孵小鸡的温床(母鸡趴窝在睡觉人的脚旁)、在炕上铺放牛粪羊粪就是育红薯苗的温床,就连夜里方便的尿盆都要摆在上面,炕还是民间艺术创作的源泉,例如,炕围画。 在前村白杨树沟的三户邻居婆姨,中间是明子婆姨,原来她家是前渠最穷的一家,现在摇身一变是最富的一家。因为过去家穷,两口子经常打架,让男人日倔了两句,老婆子气不过,寻死寻活闹腾了好几次,光是传到我耳朵里就听说上吊两次。现在光景富裕有两个来源:一是党的富民政策加上本人苦干挣来的,二是靠买卖婚姻,卖了几个家里的女子,发了一笔财。可是钱一多,明子就烧包,去赌博,听说尔格还欠人家六七百块钱。买卖婚姻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20世纪80年代初,陕北平川生活条件好的地方每个女孩一千元左右,再往上川拐沟,生活条件差的地方娶女孩要出价两千元左右,因为没人愿意出嫁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男方家庭就得多掏出一倍的价钱。六七十年代,那时女孩的价格每位才三四百元钱。用现在生活水平能出得起的价格看,三四百元就能买个丽质的女孩多便宜啊!可当初老子辛辛苦苦玩儿了命干一年,扣去口粮才挣得人民币两毛六分钱。 |
||||
 |
 |
 |
 |
 |
|
日子好过了,三天两头就想吃白面。有驴的人家磨面不用发愁,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腾出手来还可以干些别的事情,比如大家排成一溜儿,互相给对方抓头虱,梳理毛发。这是陕北民俗一大景观,如果不深入农村在庄户里住个一年半载是很难看到的。农村单干以后作为生产力工具的驴成了稀缺之物,人民公社集体化时大家都用生产队的驴,单干后无驴之户要想推磨碾米就得靠人推。就像发展生产力需要提高人口多生男孩一样,倍感生产工具紧缺的驴也要大力繁殖。那几年,人们就像着了魔似的到处买驴找种驴交配繁殖后代。村里一位叫常兴有的人家,买了个好驴种,自己又懂技术,每年靠配驴收入颇丰,他们家是全村少有的几家富户之一。 |
||||
 |
 |
 |
 |
 |
|
虽然汽车、自行车在陕北逐渐普及,但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毛驴仍是主要交通工具。你瞧两个素不相识的毛驴见了面也互相亲热起来,双方互瘙痒,这是陕北集市上常有的情景。看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景观反映到陕北民间绘画和陕北剪纸中了,仔细品味农民画和安塞剪纸,个中题材豁然开朗。优美高亢的陕北民歌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旋“骑驴婆姨赶驴的汉,手拉上毛驴回头看,命圪蛋蛋婆姨跟后边……” 他老常家的人靠配驴有了钱,富裕的生活提升了文化精神方面的需求,常家自办了一所小学,由二儿媳当老师,学生们都是本村和相隔二里外野家砭村的娃娃。国家对校舍和老师每年也补助不少。国家在当地农村不办小学,由集体和个人承办,国家给予一定补助,中学由国家办。他家还养了不少羊和秦川牛。总之,是精明之家。 现在学生娃娃都不愿上学,尤其是女孩子家里更不让上学。原因是⑴交不起学费,为生男孩儿而附带生出一大堆女孩导致家庭生活贫困化。⑵家里女孩一多,父母就不把她们看在眼里,反正将来要出嫁,要在农村劳动。⑶从投入产出上看不合算,在收入不多的情况下,花一大笔学费在女孩身上,他们一出嫁等于是给别人家培养人才。 |
||||
 |
 |
 |
 |
 |
|
信仰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而发展。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愚昧、混沌思想束缚着自己。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信仰被异化了,它被异化成发展商品市场的一种手段。在陕北被异化了的萨满教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一切向钱看。 村边路畔这个庙洞,是道光二十一辛丑1841年所建。早年路就从庙洞底下穿过,上面供奉着顺惠太王神庙的牌位,每年庙会重要祭日,从这儿路过的人们都要行三叩九拜大礼,表示对关老爷和顺惠太王的虔诚。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给砸了,如今神庙又被立了起来,还推选村里的三喜儿当了庙会会长。农村中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巫神迷信很容易泛滥,文革时期国家明令禁止,现在也不管了。这几天明子家里有人生病,就想请巫神念一回经。村里几个年轻人和四五里路远的西寺沟村后生们把鬼神从那儿引到村里,走一路耍一路,嘴里还念念有词。众乡亲们在村口等着迎候,远远看见一干人马把巫神请来,都簇拥着把神仙让到庙里安歇。庙会会长率领众乡亲上前烧香跪拜,愿神灵保佑好人平安把病魔驱走。晚上,一个巫神到明子土窑里念了一回经,前后庄人听说都来凑热闹,请巫神到自家去超度。据说巫神忙得差点没累吐了血,别人请都请不到了,因为请家太多。财源滚滚,巫神自然美不胜收,背地里乐得自己都找不着北。 听说西藏有天葬,难道是文成公主把大唐陕北的风俗带到西域不成?在陕北人死了有不同的埋法:十五岁以下去世的碎脑、猴娃是天葬,把死孩儿放到山峁子顶上,让猛禽野兽吃掉。还记得上文书说贫困户老南家了吗?为了给他的大儿子成家,老南图省钱,咬了咬牙,花两百块钱娶过一个有病的残次媳妇。这两百元钱还是倾家荡产卖光了仓窑里所有的粮食,从此,生活压得他南老汉再也没翻过身来,剩下其他的儿子都是自己掏钱娶媳妇。有病的大儿媳上厕所时生了一个娃,差点没掉到茅缸里。被猴娃“命子”所见,吓得跑回家大叫:“达,达——,把哈哩!”。没几天,孩子就死了,被南大挖撇到山峁子上。有一天,正巧老师带着学生娃娃们到山上砍柴,忽然看见碎尸骨,大家吓得四下逃散。十五岁以上女子如果死了配阴婚,就像接亲娶婆姨一样,被外庄人娶走,吹鼓手们在后面跟着吹吹打打一直到男方家,然后同死去的男人一起埋葬。娶个死媳妇要比活人少花一点,大约两百元钱左右。 |
||||
 |
 |
 |
 |
 |
|
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是肖官驿的庙会,远近闻名,就连一百多里外肤施县的人都来赶会,这个历史可追溯到过去很久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把庙砸了,所以我在这生活的六七十年代根本不知有庙会。直到一九八零年代陕北各地大搞庙宇建设,此庙才修葺一新,里面有娘娘、关公泥塑群像若干。庙会开张时戏班子也来助兴,小贩们前来卖吃、穿、用的小商品。庙宇文化促进了经济繁荣,国家也可以得到税收的好处。农历三月十八赶集,每年举行三天,这是头一天,也是最热闹的一天。 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庙会来,先花几毛钱买几把烧纸和香,放在坐落石柱上的石盆里焚烧,然后还要跪下磕几个头,以示虔诚。一帮“龟兹”吹鼓手在围墙边不停地吹着唢呐。陕北唢呐演奏历史悠久,大有发展势头。旧社会人们把唢呐吹奏者称为“龟兹”、“吹手”或“响手”,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新社会随着民间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称其为“师傅”或“手艺人”,学习吹奏的人愈来愈多,有农民、工人、干部、学生。当地文教部门扶助组织了唢呐协会,定期集训传授、交流经验,并组织竞赛发奖。 陕北唢呐杆长1.25市尺,采用不干裂的褪木(即埋在地下多年的柏木)制成。表面不予着色。其音色明亮宏厚、粗犷悍实,热烈奔放,舒展挺拔,音量大,穿透力强,渗透着雄健的阳刚之气;欢快时如火如荼,悲凉时如泣如诉;黄土高原特有的风土人情似乎一览无余地浓缩于唢呐声中,人们对美妙的吹奏音响如醉如痴的喜爱。 陕北人民千百年来,每逢婚丧嫁娶,祝贺庆典,秧歌鼓舞以及庙会聚欢等,都要请一班或几班唢呐,吹奏不同类型的乐曲予以助兴。 唢呐班子通常由五人组成,吹奏者二人,用两只相同音高的唢呐和大号,上手(或上眼)主奏高音曲调或即兴加花;下手(或下眼)助奏低八度曲调或四五度和音,相互配合默契,妙趣横生。另有司鼓(兼云锣)、小钗、圪塔锣(或称铜鼓)各一人,依据乐曲的感情,配以不同节奏。其演奏形式多样,可在坐、立、行进中吹奏,也可登台表演。 唢呐班子经常演奏的曲目,有传统曲牌、民歌小调、道情曲调和流行歌曲等,即可单曲演奏,亦可套吹(联奏),传统曲牌组成套曲时,曲牌之间通过“叫板”(或过鼓)乐段予以连接。如婚嫁、丧葬、秧歌、庆典等套曲。其板式按乐曲的不同感情和速度,分为慢板、抡板(中速)、流水板、垛板、煞头(落板)等。通常由慢到快。唢呐吹奏者,采用我国民间通用的“鼓腮”换气法、给人以一口气吹奏几十里的感觉。 |
||||
 |
 |
 |
 |
 |
|
肖官驿庙会有这么几项(举办三天),①拜神仙。上午人们从四面八方(远至延安)聚集到这里,四周有许多卖香火和纸钱的人,出上两毛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毛钱相当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块钱)就可得到用黄纸包裹的一把香,然后人们把香放到庙前石柱顶上的石盆里烧掉 ,跪地磕头。 ②然后大家鱼贯进入寺庙中抽签。根据人们求拜的目的不同抽取不同的签,有儿女签、时运签、命运签等。管抽签的人先发给你一张纸,让你烧掉,再拿签筒子在油灯上绕几下交给你。抽签人像簸谷子一样筛出一个签子掉下来,拿着签子到破签人那里查找本签号码的命运,须交两毛钱抽签费。如果你要儿女签,想生男孩,当时许下愿,第二年生了男孩上布施最少三十元,多者无限。我亲眼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反反复复抽了好几次签,命运总不好,急得她直掉眼泪。下图的破签人,就是蔡阳坪村里的拓福安,他婆姨在我们来村里之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病死了,这些年他一直没再找个婆姨,因为穷得连自己都养活不过来,还有一大堆孩子呢,自己也有点病,单干后子过得艰辛。 |
||||
 |
 |
 |
 |
 |
| ③娃娃不好养活,人们为了让娃娃平安无事,让神仙保佑,就抱着小孩来庙会这里过鬼门关。上图中可以看到专有开路的老汉左手里拿着木鱼槌,右手敲击着呼呼作响的铁片,一路走一路吆喝,让那些准备过关的人前来。院子当中放一张桌子,桌腿另一侧绑着圆环,紧挨着圆环摆着一口铡刀。有专人给小孩屁股上绑一把干草尾巴,让小孩从桌子底下爬过,当通过铁圆环时,在旁边守候的大人手握铡刀,用力把小孩屁股上捆绑的干草尾巴,象征着灾难、病魔的小鬼儿切掉。这样,人们就相信光明之神会来临,孩子以后就平安无事了。 | ||||
 |
 |
 |
 |
 |
|
④算命。趁赶庙会之际,江湖上的算命先生和各种卖狗皮膏药的人云集肖官驿庙会,他们打着“家传”、“祖传”的幌子行医算卦,还假装拿出祖传久远发黄的纸帖查找证据,然后让受骗人交钱。这里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骗人说词的情景。庙会上赌博的摊点随处可见,赌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陕北相当普遍。就拿“压明宝”来说,顷刻间有人成了富翁,有人输光了钱用实物抵押,婆姨常为这事同男人们斗阵。 那个年代,据说每年庙会上收入在三千到五千元左右。这些钱有的用作会上的开销,有的钱用来修缮寺庙,刻碑,上面记载着捐助者人名和钱款或祭祀活动大事记,剩下的钱就让那些各村的会长们瓜分了。 四月二十七日从北京出发到五月九日离开村子,我总共在延安呆了十二天,这十二天给我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我和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相处和谐融洽,他们都争先恐后叫我去自家里吃饭,为了不驳乡亲们的面子,有时一顿饭得在三四家吃,最多时一天之内吃了七八顿饭。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可是他们好客时仍然愿意拿出他们最好的食物款待亲朋好友。五月的陕北农村菜食谱是:荞面饸饹、白面、杂面、黄米糕泻(发糕)、馒头、小米粥、黄米饭、粽子、凉粉、炸黄米面油圈、炸鸡蛋面粉团、稠酒、炒鸡蛋、红烧鸡肉、酸菜、干豆角、洋芋、豆腐、粉丝、凉拌嫩苜蓿、凉拌苦菜、凉拌野生小蒜。要走的时候,乡亲们你一家我一家地往我的行李包里塞满了软糜子、酒谷米、黄米、小米、花生、干枣、鸡蛋。大家都依依不舍让我再多住几天,当我走过大平川旁的公路时,许多在地里干活的人们向我打招呼,让我过年时在回来。 路上,联社他娘忽然从人群中挤过来拉住我的手,对我悄悄耳语,让我给她女儿和她的一个外甥女在城里找对象。也不知她这话是说给我听呢还是真的让我帮忙?为什么到现在她们高中毕业还没找对象?两人一直在准备考大学,她们不甘心嫁给农村后生,想找城镇有工作、有文化的人,可是城镇的职工又不愿找乡下的姑娘,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联社要去煤矿当工人,征询我的意见是否可行,掏碳工虽然工资高,安全和肺矽病无法保障,我建议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多干两年走人。邻居老高的女儿悄悄塞给我四双她亲手绣的“喜字”、“鸳鸯”鞋垫。临走时,怎么就有那么多拉不完的话、说不完的事,让你抬不开脚、迈不出步。许多临别前感人肺腑的话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至于一辈子都铭刻在心,尽管他们的语言是朴素的。 |
||||
Copyright © 2004 mgyar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马国玉剪纸艺术创作室 2004
陕西省延安市马国玉民间剪纸艺术创作室: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工会四楼腾达公司
电话:0911-2937397 手机:13991783976 Email:
ydm2686@mgyart.com 邮政编码:716000